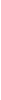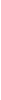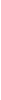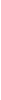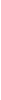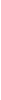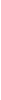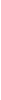武道隋唐:从五龙夺嫡开始 - 第118章 好一个房玄龄(第二更两章合一求订阅)
第118章 好一个房玄龄(第二更两章合一求订阅)
魏徵和崔氏老儒继续辩论一番之后。
崔徽华抬手示意,虽未发一言,但那份无形的威仪与决断,让那位正要反唇相讥的崔氏老儒瞬间噤声。
崔氏老儒脸上闪过一抹不甘与惶恐,终究还是躬身一礼,默然退回了西侧席位。
崔徽华適时扬声道:“第一场,论礼法纲常与取士之道”,双方已陈其词,有无再辩?”
西侧一片沉默。
崔徽华微微頷首,算是认可了此场的终结。
魏徵那番“礼之时义”与“固本安民”的论述,结合最后那记凌厉的“窃国大盗之帮閒”的定性,確实在道理与气势上占据了上风。
尤其是在这大庭广眾、太子亲临的场合,再在“礼”字上纠缠细枝末节已不明智。
“第二场,请双方辩士——立论。”
这一次,西侧席位上並未立刻有人站起。
几位核心人物,崔徽华静坐依旧,卢玄半闔著眼,王镇岳则抱著臂,目光锐利地在对面扫视。
片刻,一位卢氏老儒起身,转向主台与东侧,拱了拱手,语气刻意放缓:“適才闻听魏书生高论,有几分道理。然,治国之道,博大精深,非一“礼”字可尽括。”
“老朽不才,愿再拋一砖,以求教於太子殿下及诸位贤达一此番,可否请主张新政的一方,先行阐述?好让我等能更明悉所谓“经世致用”之学,究竟是何模样?”
说罢,他自光灼灼地看向房玄龄与魏徵。
这是以退为进,更是留了心眼。
他们吃准了杨广一方锐意进取,必然要宣扬新学,便让对方先亮出全部主张和论据,他们则可静观其变,寻找漏洞,后发制人,力求一击中的。
东侧席位上,魏徵与萧瑀对视一眼,均微微点头,目光落在中间的房玄龄身上。
房玄龄神色平静,缓缓站起,先向四方团团一揖,姿態从容不迫。
“既蒙相询,晚辈便僭越了。”
房玄龄声音清朗,不疾不徐。
“晚辈以为,今日辩论经世”与空谈”,其核心,在於辨明何为治国之实”,何为误国之虚”。我方主张,科举取士,当重经世实学,其理由有三。”
“其一,时势异也,所需之才异也。”
房玄龄他开门见山。
“古之诸侯分治,地不过百里,民不过万室,治国重在修身齐家、明礼教化。而今天下一统,郡县数百,户口千万,漕运、边备、刑名、钱粮、水利、工造————事务之繁,百倍於古。”
“若仍只以通晓经典,品行无瑕为取士唯一標准,犹如以裁衣之尺去量江河之深,其谬远矣。当今急需之才,是能理烦治剧、解决实际政务之才。此非贬低德行,而是言德需载於行,才须见於功。”
“其二,实学方能验真才。”
房玄龄继续道,条理清晰。
“经义文章,可以摹仿,可以记诵,可以清谈玄理以邀虚名。然,一道算学题目,能否解开?一桩刑狱案例,能否判明?一处河工方案,能否可行?此等实学之试,如试金石,庸才无所遁形,真才方能脱颖而出。”
“其三,亦是根本,实学直接关联国计民生,乃德政之基。”
房玄龄开始语气加重。
“圣人云:因民之所利而利之”。何为利民?非空谈仁义,而是减轻赋役、兴修水利、公正刑狱、繁荣商贸。”
“不懂钱粮,何以定赋税之轻重?不通律令,何以断狱讼之曲直?不晓地理工造,何以兴水利、筑城防?一个对民生实际一无所知或不愿知的官员,纵有爱民之心,也必行害民之政。”
“故,通实学,是践行德政不可或缺之能。將实学纳入取士標准,正是引导天下读书人,將目光从故纸堆与清谈场,转向实实在在的江山社稷与生民利病。”
房玄龄的立论,层层递进,从时势需求到人才检验,最后落脚於德政根本,逻辑严密,格局开阔。
没有激烈的抨击,却將“经世实学”的地位提升到了治国安邦不可或缺的高度,並与“德行”巧妙地进行了捆绑,指出“实学”乃“德行”在新时代的必然载体与检验標准。
台下许多有见识的人,包括一些中小世家出身的学子,都不由自主地点头。
这番道理,比单纯强调“公平”更深刻,也更能打动那些並非既得利益者,却也担心国家选才標准失当的中间派。
西侧,那位卢氏老儒认真听完,与身旁几位同僚低声交换了一下眼神,这才缓缓起身,脸上露出一丝略带讥誚的笑容。
“房书生高论,老朽听来,似乎將实学”奉为了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。”
他慢条斯理地开口。
“然而,老朽有三惑,请房先生解之。”
“其一,先生言时势所需,重实务。然则,治国仅靠实务”便可乎?立法度、定礼仪、明人伦、正风俗,此等关乎国家根本精神气象之大端,难道不需要深研经典、通达义理、德行高洁之士来执掌?若按先生之策,朝堂儘是一群只知錙铁必较、工於算计的能吏”,我大隋煌煌文明气象,与暴秦何异?此非自毁根基乎?”
“其二,先生言实学验真才。老朽想问,这实学”標准由谁而定?如何確保其公正?若主考之人自身偏好,或考题流於奇技淫巧,岂非反而將真正博通经史、胸怀韜略的大才摒之门外?科举若成,则取士之权、学问標准,尽归朝廷少数考官,此非更易为权力所垄断、所扭曲乎?”
“其三,也是老朽最忧者。”
卢氏老儒声音陡然转厉。
“先生將实学与德政捆绑,看似有理。然,若天下士子皆以通过实学”考试为晋身唯一阶梯,则必然竞相钻研术数、律令等有用之学”,而轻视修身养性、砥礪品德的“无用之功”。长此以往,士风必然变得功利、躁进、甚至不择手段。”
“为了通过考试,什么仁义廉耻皆可拋却。届时,选拔出来的,或许確是能吏”,但更可能是毫无道德底线、只知迎合上意、盘剥百姓的酷吏贪官。以术害道,祸莫大焉!”
这番反驳,同样犀利!
抓住了“实学”可能导致的“重术轻道”、“標准垄断”、“士风败坏”三大潜在弊端,句句指向科举可能引发的深层风险,並非胡搅蛮缠,而是有著深刻的忧虑。
许多原本被房玄龄说动的人,又开始动摇起来。
西侧眾人,面上露出些许得色。
这才是他们真正的反击,立足於更高层面的“道统”与“士风”忧虑。
所有人的目光再次聚焦房玄龄,看他如何应对这连环三问。
房玄龄脸上並未见慌乱,反而因对方提出了真正有价值的问题,而眼神更加专註明亮。
他略一沉吟,再次开口,语气依旧平稳。
“卢公三惑,问得极好,恰好让晚辈能將未尽之言补全。”
“答第一惑:晚辈从未言治国仅靠实务,更未言要摒弃经典义理。晚辈所言,是在通晓经典义理、具备基本德行的基础上,必须加考实学,以选拨出既明道、又能事的全才。”
“科举並非只考实学。我等的诉求,是改变唯经义是举、轻视实务的旧制,而非以实务取代经义。一个只懂实务不通经典的官员,固然是匠人。”
“但一个只通经典不懂实务的官员,於国何用?不过是华丽的点缀,甚至是祸乱的根源。我朝需要的,是能將圣人之道,用於解决实际问题的通儒”、干才”,而非只知背诵註疏的腐儒”。”
“答第二惑:关於標准与公正。乡论清议、察举推荐,其標准难道就更公正、更不易被垄断?”
“其权柄,实则分散於各地世家豪强之手,標准模糊,全凭人口一张嘴,营私舞、
党同伐异之空间,百倍於有明確章程、公开考题的科举。科举標准,可由朝廷广徵博学鸿儒、实务干吏共同议定,並定期修订,以求其公。任何制度皆非完美,然相较將选才之权完全寄託於私门品评,科举无疑更公开、更可预期、更利於寒士凭本事脱颖而出。两害相权,科举之害”远小於旧制之害”!”
“答第三惑,亦是最关键者。”
房玄龄目光如炬,直视对方。
“卢公忧心士风功利,怕选出具能无德之酷吏。请问,旧制之下,凭藉门第与清议上台的官员,便个个是道德完人么?晋之清谈误国者,岂是寒门?陈之骄奢亡身者,儘是白丁?”
房玄龄这一问,犹如利剑,直指歷史事实,让那老儒脸色一变。
“德行之养成,在於自幼家教、在於平生歷练、在於朝廷法度约束、在於风气引导,绝非仅凭是否精通某项学问所能决定。”
房玄龄声音斩钉截铁。
“科举考实学,只是设一道能干”的门槛,並未取消德行”的要求。相反,一个真正通晓民生疾苦、知道政务艰难的官员,或许比一个高高在上、只知空谈仁义的贵族子弟,更能体会何为仁政,何为爱民。將吏治腐败归咎於考试內容,实乃倒果为因,避重就轻。防止酷吏贪官,靠的是严明的法度、有效的监察、公正的考课,而非倒退回到靠出身和口碑选官的旧路。”
说到这里,房玄龄向前一步,气势已然不同。
“晚辈反倒要问卢公,若按旧制,世家子弟凭藉门荫便可平步青云,他们又有多少动力去刻苦修身、钻研实学、体验民艰?他们所恃者,唯有门第而已。此等制度,才是真正助长不学无术、骄奢淫逸、视民如草芥之无德”风气的温床。科举,正是要打破这份与生俱来的安逸,让所有人,无论出身,都必须凭真才实学、经世之能来爭取为民服务的机会。”
“这,才是最大的教化,最正的士风。”
”
”
西侧席位上,一片死寂。
那位卢氏老儒张了张嘴,脸色涨红,却发现自己准备好的层层反驳,在房玄龄这环环相扣、既有道理又有事实、既破且立的应对面前,竟被拆解得支离破碎,一时之间,竟找不到有力的切入点进行再次反驳。
对方不仅解答了他的疑惑,更反过来对旧制提出了更致命的提问。
房玄龄並未咄咄逼人,见对方语塞,便適时收住,拱手道:“晚辈浅见,或有偏颇,请卢公及诸位前辈斧正。”
崔徽华微微侧耳,仿佛在倾听那片沉默的深意。
卢玄的手指停在念珠上,王镇岳紧皱的眉头下,目光在房玄龄身上多停留了片刻。
良久,西侧无人起身再辩。
崔徽华端庄音响起:“第二场,双方已尽其辞。有无再辩?”
西侧依旧沉默。
“第二场毕。”
“好————”
“这位房兄妙级————”
台下,压抑的振奋在寒门学子与眾多平民中荡漾开来。
“甚好,这世间可以说得过魏徵和房玄龄的人,可真不多。”
杨广暗暗窃喜,这便是他自信的由来。
而楼上雅间,一些南方来的勛贵,眼中则闪烁著深思与评估的光芒。
经此两场,新政一方,不仅在“理”上站稳,更在“辩”的智慧与气度上,开始真正显露锋芒。
李世民,紧紧握著小拳头,眼中全是对这种智慧交锋的嚮往与折服。
短暂的休憩间隙结束,崔徽华正准备宣布第三场辩题。
然而,未等她开口一一股沉重如山的磅礴威压,毫无徵兆地、决绝地从西侧轰然爆发。
这次出手的,並非卢玄那古朴文雅的文脉厚重,也不是王镇岳那金戈铁马的沙场煞气0
而是数名端坐在后排、一直沉默不语的世家宿老,几乎同时睁开了他们半闔的眼眸。
这些人,或许並非以学问闻名,但皆是各大世家蓄养或出身,修为至少在两甲子门槛的武者宿老!
他们平日隱於幕后,此刻却被接连的“失利”激起了真怒。
数道性质各异却同样强横的內劲气息,如同无形的枷锁与巨锤,混合著他们长久以来身居上位、视寒门如草芥的精神意志,凝成一股不容置疑的恐怖压力,直接朝著东侧席位上的魏徵、房玄龄、萧瑀三人狠狠压去。
“呃!”
首当其衝的魏徵闷哼一声,脸色瞬间煞白。
他文气刚直,但武者修为尚浅,在这等混合了精神力的威压面前,仿佛孤舟面对海啸,只觉得呼吸困难,神魂震盪,那挺直的腰杆都不由自主地微微一晃。
房玄龄稍好,他心性沉稳,武者內劲稍许。但也眉头紧锁,额角渗出细汗,仿佛背负了千钧重担,连思维似乎都变得迟滯起来。
萧瑀也是文官,武者內劲也低,更是身形一晃,若非手疾眼快扶住案几,几乎要坐立不稳,胸中气血翻腾,官袍下的手指深深掐入掌心。
无形的压力如有实质,让东侧席位上的空气都仿佛凝固了。
台下离得近的寒门学子与民眾,哪怕只是被余波扫到,也感到一阵心悸气短,纷纷骇然后退。
台上气氛,骤然降至冰点。
就在魏徵三人咬牙苦撑,几乎要被这股联合威压彻底压垮心神之际。
“哼。
,,一声带著毫不掩饰嘲弄之意的冷哼,从北台主位传来。
声音不高,却像一柄利刃,轻易划破了那凝固沉重的压力帷幕。
紧接著,眾人只见主位上那位玄衣太子,只是隨意地抬起右手,修长的手指在空中轻轻一拂。
动作隨意得如同掸去衣襟上的微尘。
添加书签
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/提交/前进键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