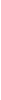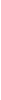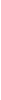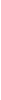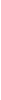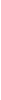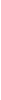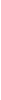穿梭两界:我到1950建机械厂 - 第115章 沈静
第115章 沈静
精密车床的生產,需要更精细的技术和更高的能力。
要扩大生產,就需要有一群合格的技术和工人。
所以选拔人才就成为5號车间规模生產前的必要准备。
而这次选拔中,一个女工在其中脱颖而出。
这也是许多人没有想到的事。
她就是第一批加入前进厂金工车间的女工沈静。
说起来她的故事还是非常励志的,也代表了这个时代巨大的变迁。
1938年的南昌,空气中瀰漫著恐慌和硝烟的味道。
七岁的沈静,穿著打补丁的灰布衫,手里紧紧攥著母亲给她的几个铜板,任务是用这点钱买回全家一天的口粮—一些发黄的糙米和一小把乾菜。她不是一个人,身后还跟著她五岁的弟弟沈康,弟弟肩上挎著一个洗得发白的布书包,那是全家最体面的物件。
沈家的日子紧巴巴。
父亲是码头扛包的苦力,母亲给人家浆洗衣物,收入微薄。
——
沈静作为长女,从小就要分担家务,照看弟弟妹妹。
唯一的光亮和希望,都寄托在弟弟沈康身上—父母咬牙决定,再苦也要送这个男孩去念几天书,盼著他能识文断字,將来或许能有个出息,改变家庭的命运。
去往米店的路上,会经过当时的nc市立第二小学。
学校那圈不算高的围墙,对於沈静来说,却像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。
她总是拉著弟弟,在校门口不远处停下,看著那些穿著整齐的学生们蹦蹦跳跳地走进校门,听著里面传来的、模糊却整齐的读书声。
那是另一个世界,一个与她无关的世界。
“姐,快走啊,要迟到了。”沈康催促著,他对学校充满嚮往,也有些著急。
沈静回过神来,眼神黯淡了一下,隨即露出一个属於长姐的、带著点早熟韧劲的笑容:“好,送你去。”
把弟弟送到校门口,看著他小小的身影消失在教室方向,沈静並没有立刻离开。
她绕到学校后墙一处僻静的角落,那里有棵老槐树,枝叶伸到了墙外。她熟练地从墙根一个不起眼的破洞里掏出一个小布包,里面是她从家里带来的碎布头和针线。
她就坐在槐树下的石头上,一边就著天光缝补一件弟弟磨破的裤子,一边竖起耳朵,捕捉著隨风飘出围墙的讲课声。
“人、手、足、口、耳、目————”
“天地玄黄,宇宙洪荒————”
“锄禾日当午,汗滴禾下土————”
先生抑扬顿挫的声音,孩子们稚嫩的跟读,像甘泉一样流入沈静乾渴的心田。她听不懂“宇宙洪荒”,但“人手足口”她记下了;她不明白“玄黄”何意,但“锄禾日当午”
的画面让她想起父母在田间地头的辛劳。
她用捡来的树枝,在泥地上偷偷地比划著名那些字的形状。针线活是她的掩护,听课才是她真正的自的。这是她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,虽然短暂,且冒著被校工驱赶的风险。
这样的“偷学”日子,持续了几年。她不仅认识了越来越多的字,甚至还能听懂一些简单的算术和道理。弟弟放学回家做功课时,她就在一旁借著微弱的光线做针线,耳朵却竖著,心里默默跟著弟弟念。
有时弟弟遇到难题,她还能凭著偷听来的记忆,磕磕绊绊地提醒一两句,让弟弟惊讶不已:“姐,你怎么知道?”
平静的“偷学”日子被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彻底踏碎。
nc沦陷前,恐慌席捲全城。沈家隨著逃难的人流,仓皇离开家园,奔向未知的、据说相对安全的乡下。路上混乱不堪,哭声、喊声、飞机的轰鸣声交织在一起。
在一次躲避飞机轰炸的慌乱中,沈静和家人跑散了。
她躲在一个被炸塌了半边的祠堂断墙后,嚇得浑身发抖。轰炸间隙,她在废墟中摸索,想找点能吃的东西或能用的东西。她的手没有摸到食物,却在一堆瓦砾下,触到了一个硬硬的东西那是一本被烧焦了边角、浸了水、封面模糊不清的《千家诗》。还有半本被撕烂的《算术入门》。
她如获至宝,也顾不上害怕了,小心翼翼地把这两本破烂不堪的书塞进怀里,仿佛揣著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。后来,她幸运地找到了失散的父母和弟弟妹妹,一家人继续在乡间顛沛流离。
在逃难落脚的一个破败村子里,生活极其艰苦。沈静要跟著大人去挖野菜、捡柴火、
帮人干杂活换点吃的。但无论多累,她总会挤出一点时间,躲在山坡后、草垛边,拿出那两本捡来的破书。
字认不全,她就连蒙带猜;算术题看不懂,她就用树枝在地上画。知识的微光,在战乱的废墟和生活的重压下,顽强地闪烁著,成了她精神上唯一的慰藉和支撑。她隱隱觉得,这些“字”和“数”,是重要的,是通向那个她无法进入的“学校世界”的钥匙。
时间过的非常快,抗战胜利,新中国成立。nc城焕发出新的生机。政府大力开展扫除文盲运动,在各个街道、厂矿开办了免费的扫盲班。
沈家所在的街道也贴出了通知。已经十六七的沈静,心里那簇渴望知识的火苗,再次被点燃了。
她鼓起勇气,走进了街道办事处的扫盲班报名点。
负责登记的是个戴眼镜的年轻干部。他问:“姓名?年龄?以前念过书吗?”
沈静小声回答:“沈静,16岁,没————没正式念过。”
干部点点头,准备把她分到零基础班。沈静犹豫了一下,还是怯生生地补充道:“同志,我————我认得一些字,也会算点简单的数。”
干部有点意外,推了推眼镜:“哦?你认得多少?写几个看看。”
沈静拿起笔,有些紧张,但还是工工整整地写下了“新中国”、“共產党”、“毛主席”、“工人”、“农民”等字,还写出了自己的名字和简单的加减法。
干部惊讶地看著她娟秀的字跡和清晰的逻辑,这绝不是零基础的水平。“沈静同志,你这文化水平不低啊!在哪学的?”
沈静红著脸,低声讲述了自己“偷听”和“捡书自学”的经歷。
干部听后十分动容,感慨道:“了不起!旧社会埋没了多少人才!你这样有基础、有毅力的同志,应该起到带头作用。你別当学员了,来当我们扫盲班的助教,帮著教那些完全不识字的街坊邻居,怎么样?”
就这样,沈静成了扫盲班里特殊的“女先生”。她教得极其耐心,因为她深知不识字的苦和渴望识字的心。她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,用最浅显的语言讲解,深受学员们的尊敬和喜爱。
她的名声甚至传到了区里,被评为了“扫盲积极分子”。
后来,国家扩大师范教育,区里还推荐她去参加师范学校的短期培训,並暗示,只要顺利结业,有很大机会可以分配到小学当一名正式教师。
就在沈静沉浸在即將实现“教师梦”的喜悦中时,家庭的变故像一盆冷水浇了下来。
父亲在码头常年超负荷的劳动,落下了严重的腰伤和肺病,这一次突然加重,臥床不起,几乎失去了劳动能力。母亲终日以泪洗面,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正在念书,家里的顶樑柱塌了。
那天晚上,沈静拿著那张珍贵的师范培训通知书,在父亲低沉的咳嗽声和母亲的嘆息声中,辗转难眠。
当一名人民教师,站在讲台上传播知识,这是她梦里都不敢想的美好未来,是她黑暗童年里微弱却始终不灭的光亮。如今,这光亮就在触手可及的地方。
可是,现实是冰冷的。
师范培训期间补贴微薄,根本无法支撑家庭。如果她去上学,全家可能连饭都吃不上。她是长女,是姐姐,父母年迈,弟妹幼小,这个家需要她立刻扛起来。
第二天清晨,她眼睛红肿地找到了街道干部和师范学校的负责人,声音哽咽但异常清晰地说明了情况,艰难地放弃了这次培训机会。
干部们虽然惋惜,但也理解她的难处。母亲抱著她痛哭,说她拖累了女儿。沈静摇摇头,擦乾眼泪,语气坚定地说:“妈,没事,有我在,这个家垮不了。”
就在沈静为生计发愁,准备去码头或纱厂找些更苦更累的零活时,她听到了一个消息:城里的“前进机械厂”正在招工,而且专门招收一批女工!消息还说,前进厂是市里的重点厂,工资待遇比一般地方高,还有非常好劳保福利。
这个消息,像一道新的光,照进了沈静灰暗的生活。
虽然“机械厂”、“车床”这些词对她来说十分陌生,甚至有些令人畏惧,但“工资高、待遇好”这六个字,对她有著致命的吸引力。
这可能是她既能养活全家,又能获得一份稳定、有前途的工作的最佳机会。
然而,她的决定遭到了父母的反对。父亲躺在床上,喘著气说:“静静啊——那机械厂,都是抡大锤、跟铁疙瘩打交道的活,又脏又累,那是男人干的————你一个姑娘家,去受那个罪干啥?不如找个轻省点的活————”
母亲也忧心忡忡:“听说那机器轰隆隆响,嚇死人,万一不小心————”
沈静这次没有妥协。她耐心地对父母说:“爸,妈,现在新社会了,男女平等。国家號召妇女也能顶半边天。前进厂是正规大厂,安全有保障。工资高,弟弟妹妹的学费、家里的开销就都有著落了。这是我改变命运的机会,我想去试试。”
她骨子里那种在困境中磨礪出的坚韧和主见,此刻发挥了作用。她毅然去报了名。
招工考核时,沈静再次让招工於部眼前一亮。
大部分来应聘的女工文化程度不高,很多是纯文盲。而沈静不仅能流利地读写,还能进行简单的数学运算,逻辑清晰,谈吐稳重。
她“扫盲班女先生”的经歷,更是加分项。
厂里正需要这种有文化、有耐心、能培养成技术骨干的苗子。她毫无悬念地被第一批录取。
1953年春,沈静和一批同龄女工,怀著忐忑和憧憬,走进了前进机械厂的大门。
高大的厂房、轰鸣的机器、空气中瀰漫的机油和金属切削液的味道,一切都那么新奇而又充满挑战。
厂里给新女工提供了几个岗位选择:相对轻鬆的仓库保管员、厂部文书,或者劳动强度较大但工资更高的金工车间操作工。
几乎所有人都劝沈静选择前两者,毕竟她有文化,坐办公室更“体面”。
沈静站在车间门口,看著那些飞速旋转的卡盘、闪烁著寒光的车刀,以及工人们专注的神情,心里也有些打鼓。但当她听到老师傅介绍,金工是机械製造的核心,技术含量高,晋升空间大,最高工资能比文书高出近一倍时,她几乎没有犹豫。
“我选金工车间。”她平静地说。还是那个最现实的理由—钱,能更快地让家人过上好日子。同时,內心深处,那种对挑战的渴望,对掌握一门“硬核”技术的嚮往,也悄然萌动。
她被分配跟著金工车间技术最好的老师傅之一魏长水学习。
魏师傅是个严肃、不苟言笑的老工人,技术精湛,要求极其严格。
起初,他对带女徒弟有些疑虑,觉得女孩子力气小,吃不了这份苦,而且车床操作精细又危险。
沈静用行动打消了师傅的疑虑。她不怕脏不怕累,上班最早到,下班最晚走。
魏师傅讲解时,她眼睛一眨不眨地听著,手里拿著个小本子,拼命地记。练习磨车刀,她的手被砂轮磨破过;装卸工件,她的胳膊累得抬不起来;学习看图纸,她常常熬夜研究到眼睛发酸。
但她从不叫苦,那股子狠劲和韧劲,让车间里的男工们都暗自佩服。
魏师傅渐渐对她刮目相看,开始倾囊相授。从最基础的识图、量具使用,到车刀的角度磨削、切削用量的选择,再到复杂零件的工艺安排————沈静像一块海绵,疯狂地吸收著知识。她的文化基础此时发挥了巨大作用,理解图纸和工艺卡片比一般人快得多,计算转速、进给量也格外精准。
到1955年底,沈静已经能够独立操作c620车床,加工出符合精度要求的轴、套、齿轮坏等复杂零件,成了金工车间名副其实的骨干,工资也涨了上去,成了家里名副其实的顶樑柱。
父母看到她拿回家的钱和获得的奖状,终於从最初的反对变成了由衷的骄傲。
1956年初,厂里决定组建专门的精密工具机车间,需要从各车间抽调最顶尖的技术工人。
选拔標准极其苛刻,除了技术过硬,更要求心细如髮、沉稳耐心,能適应恆温环境和高精度要求。
消息传出,金工车间议论纷纷。很多人都想去,但也知道难度极大。
魏师傅找到沈静,语重心长地说:“小沈,这是个好机会,也是块硬骨头。精密工具机的精度是微米级的,差一丝一毫都不行。你心思细,手稳,文化底子好,我觉得你可以去试试。”
沈静心动了,这意味著进入工厂技术的最高殿堂,接触最先进的设备和技术。但竞爭无疑非常激烈,对手都是厂里顶尖的老师傅和优秀青工。
选拔考试包括理论笔试和实际操作。理论部分,沈静凭藉扎实的文化基础和对工艺的深刻理解,取得了高分。实际操作是现场加工一个高精度的主轴套筒,要求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都达到极其严格的標准。
考场设在临时布置的恆温间,气氛紧张。
沈静深吸一口气,像平时一样,先仔细审图,核对坯料,然后选择合適的车刀,精心磨削刀尖角度。
安装工件时,她反覆用千分尺校准,確保装夹同心度。切削过程中,她全神贯注,听著刀具与工件接触时声音的细微变化,观察著切屑的顏色和形状,適时调整进给量和转速。她的动作流畅、稳定,没有丝毫多余和慌乱。
最终,她加工出的零件,经计量室检测,各项指標完全符合图纸要求,甚至在某些次要尺寸上还略有盈余。她的沉稳、细致和精准,给考核组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当她得知自己成功入选精密工具机车间名单时,激动得差点掉下眼泪。
这不仅仅是一份新工作,更是对她多年来坚持、努力和技艺的最高认可。从那个在围墙外“偷听”的小女孩,到扫盲班的女先生,再到如今站在工厂技术金字塔尖的精密技工,她走过的路,布满荆棘,却也开满了奋斗的花朵。
她站在即將投入使用的、窗明几净的恆温车间门口,看著里面那些散发著冷峻金属光泽的高精度磨床、坐標鏜床,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。她知道,一个新的、更富有挑战的征程,即將开始。
而她,沈静,已经准备好了。她的故事,是成千上万在新中国工业化浪潮中,用智慧和汗水改变自身命运、亦推动国家前进的普通女性的缩影。
添加书签
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/提交/前进键的